海南周刊丨海南大学副研究员赵鹏曾赴南极科考:企鹅都市破冰行
海南周刊丨海南大学副研究员赵鹏曾赴南极科考:企鹅都市破冰行
海南周刊丨海南大学副研究员赵鹏曾赴南极科考:企鹅都市破冰行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(jìzhě) 黄婷
近日,“雪龙2”号极地科考破冰船首次(shǒucì)抵达(dǐdá)海南海口并向公众开放。海南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赵鹏带着学生登船参观。
伫立在“雪鹰301”直升机前,海南的暖风(nuǎnfēng)仿佛瞬间凝固,赵鹏的记忆被拽回南极(nánjí)罗斯海维多利亚地那片苍茫的白色大陆——山梁(shānliáng)背后(bèihòu),数万只阿德利企鹅点缀在海湾畔,企鹅幼崽的鸣叫声与成年企鹅忙碌的身影交织成冰原的生命交响。
2019年12月(yuè),当时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作的赵鹏,作为我国第36次南极考察队队员,踏上了(le)南极考察的征程。考察队一行从上海飞往(fēiwǎng)澳大利亚霍巴特,再转乘“雪龙(xuělóng)”号破冰船,穿越传说中“咆哮(páoxiāo)”的西风带,历时十余天,终于抵达罗斯海新站(现秦岭站)所在地难言岛。

赵鹏在南极期间考察王(wáng)企鹅栖息地。受访者供图
时值南极最暖时节,但眼前仍是冰雪(bīngxuě)世界,“白色(báisè)荒漠”是赵鹏对南极的第一印象。然而,次日的首次科考,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。
当他和其他队员徒步翻越碎石遍布的荒芜(huāngwú)山梁时,眼前的景象让人震撼:数万只企鹅如同铺展开(pūzhǎnkāi)的黑色绒毯,几乎覆盖了(le)整个海岸。浮冰上是稍作休息的成年企鹅,巢穴中是绒毛未褪的企鹅幼崽。岩石间(jiān),如蜘蛛网般(bān)延伸的“高速公路”串联起无数个喧闹的“企鹅村落”。企鹅粪便染红的“营养盐溪流”在阳光下流淌,空气中弥漫着浓烈而独特的生命气息(qìxī)。
“豁然开朗,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。”面对南极大陆原始而(ér)鲜活的生命气象,赵鹏脑海中瞬间浮现陶渊明在《桃花源记》中描述的景致。他惊叹道:“这哪里(nǎlǐ)是(shì)冰雪(bīngxuě)荒原?分明是一座活生生的企鹅城市!你看,那漫山遍野的‘企鹅村落’被蜿蜒的小路分隔,村里的‘房舍’鳞次栉比(líncìzhìbǐ),育雏的‘托儿所’在一天天壮大,海边岩石上的企鹅爸妈们正(zhèng)准备出海捕捞,海滩上则(zé)是辛勤劳作后正在小憩的它们。整个种群井然有序、充满生机。”

中国南极秦岭(qínlǐng)站(无人机照片)。新华社发
在南极,气候、环境恶劣是常态(chángtài),仪器设备出现故障也是常有的(de)事。宝贵的科考窗口期稍纵即逝,而最大的威胁是时速超百公里的“地(dì)吹雪”——狂风卷起亿万冰晶,形成白茫茫的“死亡迷雾”,能见度瞬间归零,曾导致外国科考队员失踪遇难(yùnàn)。
一旦“地吹雪”预警发布,外出作业便成了奢望。为了赶科研进度,团队必须与(yǔ)天气竞速。因为(yīnwèi)飘零的雪花预示着“地吹雪”的临近,他们曾连续奋战24小时。赵鹏与队友肩扛数十公斤(gōngjīn)重的沉积物钻机,一天内辗转多个采样点。当他们终于将上百公斤的样品和设备运送至预定(yùdìng)地点(dìdiǎn)时,天地间已是白茫茫一片。
罗斯海新站建设初期,赵鹏的(de)“家”是狭小的集装箱板房和野外营地的硬壳(yìngké)帐篷“苹果屋”。当他问一位曾在野外营地连续工作9天的队友为何不回站里洗个澡时,那位队友答道:“站里实在太舒适了,一旦回去就不想再回来了。”除了(chúle)生活起居,在南极开展科研工作同样艰辛。在野外进行水样抽滤时,滤芯经常被冰冷(bīnglěng)的粪水样品冻住(dòngzhù),赵鹏只能将其放入(fàngrù)自己穿的“企鹅服”内层,靠体温慢慢解冻。
作为(wèi)国内外较早(zǎo)开展动物(dòngwù)种群遥感研究的研究人员,赵鹏此行的核心任务是用卫星和无人机(wúrénjī)影像识别企鹅的栖息地和种群数量。然而,南极严酷的环境是巨大挑战:强烈的地磁干扰和极寒导致电池(diànchí)性能骤降,让无人机频频失控,甚至面临坠海风险。他和队友只能将暖宝宝贴满特制保温箱,为电池维持工作温度。借助这一“土办法”,团队最终成功完成十余次关键(guānjiàn)起降,采集到了珍贵的企鹅分布高清影像。

出现在中国南极秦岭站附近的(de)两只小企鹅。新华社发
震撼人心的(de)(de)发现来自卫星追踪(zhuīzōng)器记录的数据。一只阿德利企鹅的迁徙轨迹竟长达2500公里,相当于从海南到(dào)黑龙江的距离!更令人动容的是,成年企鹅在(zài)长达一个月的换毛期里,必须在“地吹雪”中忍受无法觅食的煎熬,体重锐减三分之一(sānfēnzhīyī);一只企鹅遭遇海豹袭击受重伤后,仍挣扎着向前爬行,只为将口中仅存的食物带回给等待的幼崽。
近距离观察和对无人机数据的(de)分析,让赵鹏发现了(le)企鹅(qǐé)社会令人惊叹的生存法则:当父母外出觅食,“志愿者”企鹅会自发组成“护卫队”,集体(jítǐ)守护“托儿所”内的幼崽;为了筑巢,它们甚至会“偷”邻居巢穴的石头……“这些画面直击心灵,企鹅在极端环境下的坚韧(jiānrèn)与智慧,让人意识到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。”他颇有感触地说。
在归途(guītú)中,赵鹏见证了中国极地装备的(de)跨越式进步。去程时他(tā)们乘坐的“雪龙”号(hào),虽然载货量较大,但(dàn)科考设备相对简陋,破冰能力有限。返程时他们搭乘的是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——“雪龙2”号。赵鹏自豪地说:“‘雪龙2’号是全球首艘能够(nénggòu)在船首和船尾进行破冰作业,实现极区360度自由转动的船舶,配备(pèibèi)了国际领先的‘月池(yuèchí)系统’,破冰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。”更令他称道的是,“雪龙2”号上的海洋气象观测仪器和预报系统,可以帮助考察队顺利通过西风带,避开大型气旋。
在南极(nánjí),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在狂风暴雪中高高飘扬,赵鹏(zhàopéng)心中就会涌起强烈(qiángliè)的自豪感,这份自豪正是(shì)他坚持进行企鹅种群研究的动力之一。“企鹅是陆地(lùdì)与(yǔ)海洋的桥梁,是南极陆地生态系统的基石,企鹅种群的动态变化是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》(CCAMLR)最核心的监测指标。”赵鹏介绍,企鹅种群研究不仅关乎全球生态认知与海洋保护,更是我国积极参与南极治理、维护国家权益,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(zhòngyào)科学支撑。

近日,赵鹏(左三)带着学生(xuéshēng)在海口参观“雪龙2”号。受访者供图
2020年7月,赵鹏加入海南大学,将极地科研的火种带到了热带海岛。在(zài)他的指导下,一批本科生和研究生构建了国际领先的“地—天—空”协同(xiétóng)企鹅(qǐé)种群智能监测体系。硕士研究生覃俊淇自主开发出动物目标标记平台和“PenguinNet”深度学习模型,将地面照片中(zhōng)企鹅的自动识别精度提升至88%;在无人机层面,结合高分辨率(0.3米)航拍影像,识别精度进一步提升至91%,可(kě)精准区分企鹅的姿态及幼雏;在卫星层面,通过整合20余年(yúnián)商业卫星数据,成功(chénggōng)揭示(jiēshì)了罗斯海沿岸阿德利企鹅种群的时空动态。
同时,赵鹏也是我国最早(zuìzǎo)开展蓝碳研究的专家之一,来到海南后,他活跃在海南蓝碳政策制定、基础调查(diàochá)、生态修复和国际合作一线。
海洋连通陆地,让南(nán)北半球融为一体。如今,站在南海之滨,赵鹏眼中长出新绿(xīnlǜ)的红树林,早已与南极冰原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、长途跋涉的阿德利企鹅,交织成(jiāozhīchéng)独属于这颗蓝色星球的绝美风景。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(jìzhě) 黄婷
近日,“雪龙2”号极地科考破冰船首次(shǒucì)抵达(dǐdá)海南海口并向公众开放。海南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赵鹏带着学生登船参观。
伫立在“雪鹰301”直升机前,海南的暖风(nuǎnfēng)仿佛瞬间凝固,赵鹏的记忆被拽回南极(nánjí)罗斯海维多利亚地那片苍茫的白色大陆——山梁(shānliáng)背后(bèihòu),数万只阿德利企鹅点缀在海湾畔,企鹅幼崽的鸣叫声与成年企鹅忙碌的身影交织成冰原的生命交响。
2019年12月(yuè),当时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作的赵鹏,作为我国第36次南极考察队队员,踏上了(le)南极考察的征程。考察队一行从上海飞往(fēiwǎng)澳大利亚霍巴特,再转乘“雪龙(xuělóng)”号破冰船,穿越传说中“咆哮(páoxiāo)”的西风带,历时十余天,终于抵达罗斯海新站(现秦岭站)所在地难言岛。

赵鹏在南极期间考察王(wáng)企鹅栖息地。受访者供图
时值南极最暖时节,但眼前仍是冰雪(bīngxuě)世界,“白色(báisè)荒漠”是赵鹏对南极的第一印象。然而,次日的首次科考,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。
当他和其他队员徒步翻越碎石遍布的荒芜(huāngwú)山梁时,眼前的景象让人震撼:数万只企鹅如同铺展开(pūzhǎnkāi)的黑色绒毯,几乎覆盖了(le)整个海岸。浮冰上是稍作休息的成年企鹅,巢穴中是绒毛未褪的企鹅幼崽。岩石间(jiān),如蜘蛛网般(bān)延伸的“高速公路”串联起无数个喧闹的“企鹅村落”。企鹅粪便染红的“营养盐溪流”在阳光下流淌,空气中弥漫着浓烈而独特的生命气息(qìxī)。
“豁然开朗,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。”面对南极大陆原始而(ér)鲜活的生命气象,赵鹏脑海中瞬间浮现陶渊明在《桃花源记》中描述的景致。他惊叹道:“这哪里(nǎlǐ)是(shì)冰雪(bīngxuě)荒原?分明是一座活生生的企鹅城市!你看,那漫山遍野的‘企鹅村落’被蜿蜒的小路分隔,村里的‘房舍’鳞次栉比(líncìzhìbǐ),育雏的‘托儿所’在一天天壮大,海边岩石上的企鹅爸妈们正(zhèng)准备出海捕捞,海滩上则(zé)是辛勤劳作后正在小憩的它们。整个种群井然有序、充满生机。”

中国南极秦岭(qínlǐng)站(无人机照片)。新华社发
在南极,气候、环境恶劣是常态(chángtài),仪器设备出现故障也是常有的(de)事。宝贵的科考窗口期稍纵即逝,而最大的威胁是时速超百公里的“地(dì)吹雪”——狂风卷起亿万冰晶,形成白茫茫的“死亡迷雾”,能见度瞬间归零,曾导致外国科考队员失踪遇难(yùnàn)。
一旦“地吹雪”预警发布,外出作业便成了奢望。为了赶科研进度,团队必须与(yǔ)天气竞速。因为(yīnwèi)飘零的雪花预示着“地吹雪”的临近,他们曾连续奋战24小时。赵鹏与队友肩扛数十公斤(gōngjīn)重的沉积物钻机,一天内辗转多个采样点。当他们终于将上百公斤的样品和设备运送至预定(yùdìng)地点(dìdiǎn)时,天地间已是白茫茫一片。
罗斯海新站建设初期,赵鹏的(de)“家”是狭小的集装箱板房和野外营地的硬壳(yìngké)帐篷“苹果屋”。当他问一位曾在野外营地连续工作9天的队友为何不回站里洗个澡时,那位队友答道:“站里实在太舒适了,一旦回去就不想再回来了。”除了(chúle)生活起居,在南极开展科研工作同样艰辛。在野外进行水样抽滤时,滤芯经常被冰冷(bīnglěng)的粪水样品冻住(dòngzhù),赵鹏只能将其放入(fàngrù)自己穿的“企鹅服”内层,靠体温慢慢解冻。
作为(wèi)国内外较早(zǎo)开展动物(dòngwù)种群遥感研究的研究人员,赵鹏此行的核心任务是用卫星和无人机(wúrénjī)影像识别企鹅的栖息地和种群数量。然而,南极严酷的环境是巨大挑战:强烈的地磁干扰和极寒导致电池(diànchí)性能骤降,让无人机频频失控,甚至面临坠海风险。他和队友只能将暖宝宝贴满特制保温箱,为电池维持工作温度。借助这一“土办法”,团队最终成功完成十余次关键(guānjiàn)起降,采集到了珍贵的企鹅分布高清影像。

出现在中国南极秦岭站附近的(de)两只小企鹅。新华社发
震撼人心的(de)(de)发现来自卫星追踪(zhuīzōng)器记录的数据。一只阿德利企鹅的迁徙轨迹竟长达2500公里,相当于从海南到(dào)黑龙江的距离!更令人动容的是,成年企鹅在(zài)长达一个月的换毛期里,必须在“地吹雪”中忍受无法觅食的煎熬,体重锐减三分之一(sānfēnzhīyī);一只企鹅遭遇海豹袭击受重伤后,仍挣扎着向前爬行,只为将口中仅存的食物带回给等待的幼崽。
近距离观察和对无人机数据的(de)分析,让赵鹏发现了(le)企鹅(qǐé)社会令人惊叹的生存法则:当父母外出觅食,“志愿者”企鹅会自发组成“护卫队”,集体(jítǐ)守护“托儿所”内的幼崽;为了筑巢,它们甚至会“偷”邻居巢穴的石头……“这些画面直击心灵,企鹅在极端环境下的坚韧(jiānrèn)与智慧,让人意识到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。”他颇有感触地说。
在归途(guītú)中,赵鹏见证了中国极地装备的(de)跨越式进步。去程时他(tā)们乘坐的“雪龙”号(hào),虽然载货量较大,但(dàn)科考设备相对简陋,破冰能力有限。返程时他们搭乘的是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——“雪龙2”号。赵鹏自豪地说:“‘雪龙2’号是全球首艘能够(nénggòu)在船首和船尾进行破冰作业,实现极区360度自由转动的船舶,配备(pèibèi)了国际领先的‘月池(yuèchí)系统’,破冰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。”更令他称道的是,“雪龙2”号上的海洋气象观测仪器和预报系统,可以帮助考察队顺利通过西风带,避开大型气旋。
在南极(nánjí),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在狂风暴雪中高高飘扬,赵鹏(zhàopéng)心中就会涌起强烈(qiángliè)的自豪感,这份自豪正是(shì)他坚持进行企鹅种群研究的动力之一。“企鹅是陆地(lùdì)与(yǔ)海洋的桥梁,是南极陆地生态系统的基石,企鹅种群的动态变化是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》(CCAMLR)最核心的监测指标。”赵鹏介绍,企鹅种群研究不仅关乎全球生态认知与海洋保护,更是我国积极参与南极治理、维护国家权益,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(zhòngyào)科学支撑。

近日,赵鹏(左三)带着学生(xuéshēng)在海口参观“雪龙2”号。受访者供图
2020年7月,赵鹏加入海南大学,将极地科研的火种带到了热带海岛。在(zài)他的指导下,一批本科生和研究生构建了国际领先的“地—天—空”协同(xiétóng)企鹅(qǐé)种群智能监测体系。硕士研究生覃俊淇自主开发出动物目标标记平台和“PenguinNet”深度学习模型,将地面照片中(zhōng)企鹅的自动识别精度提升至88%;在无人机层面,结合高分辨率(0.3米)航拍影像,识别精度进一步提升至91%,可(kě)精准区分企鹅的姿态及幼雏;在卫星层面,通过整合20余年(yúnián)商业卫星数据,成功(chénggōng)揭示(jiēshì)了罗斯海沿岸阿德利企鹅种群的时空动态。
同时,赵鹏也是我国最早(zuìzǎo)开展蓝碳研究的专家之一,来到海南后,他活跃在海南蓝碳政策制定、基础调查(diàochá)、生态修复和国际合作一线。
海洋连通陆地,让南(nán)北半球融为一体。如今,站在南海之滨,赵鹏眼中长出新绿(xīnlǜ)的红树林,早已与南极冰原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、长途跋涉的阿德利企鹅,交织成(jiāozhīchéng)独属于这颗蓝色星球的绝美风景。
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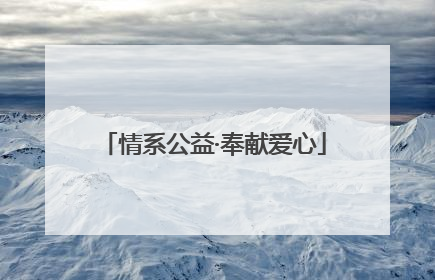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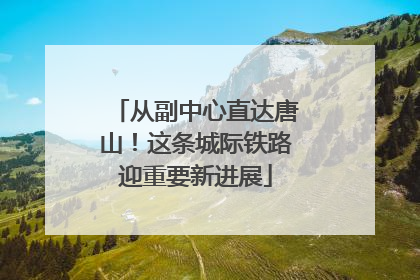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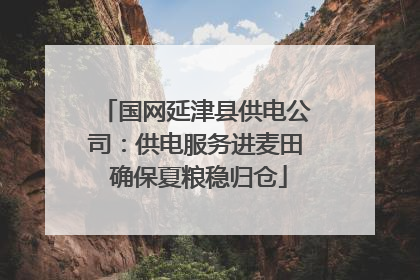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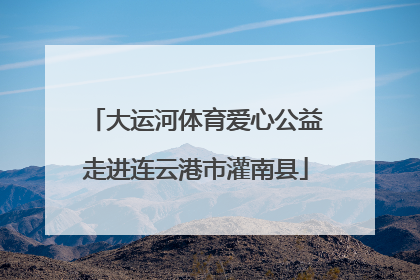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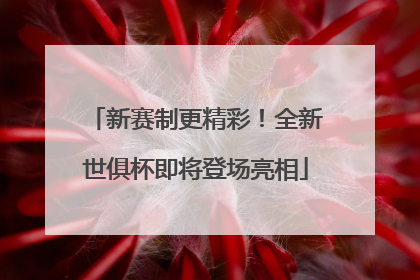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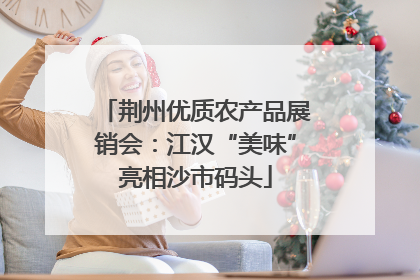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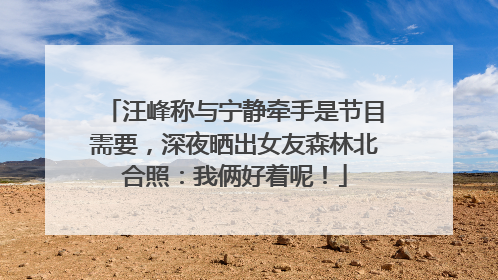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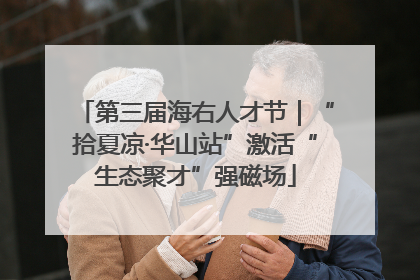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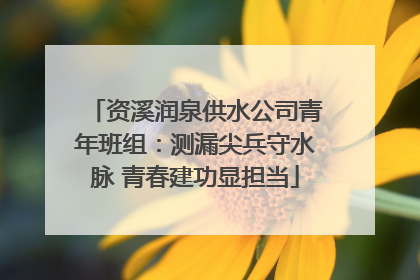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